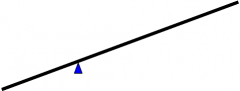中信建投:日本泡沫之后杠杆去化之路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实施了多年量化宽松,持续低利率将更多“廉价”日本资金泵到全球市场,这既是理解全球美元流动性的重要一环(日本套息交易深刻影响美元流动性),也是理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低利率中枢的关键。
而之所以日本奉行较长时间低利率,重要原因是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私人部门经历了漫长的去杠杆,只有财政在持续扩表。一面是私人缩表,一面是政府扩表,货币只能选择极度宽松。
正是私人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杠杆腾挪,深刻影响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资本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流动性驱动叙事。
在“失去的”三十年间,居民和私营企业在内的私人部门停止扩表,开始去杠杆。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扩张,最终超过了250%。
泡沫前后,日本各部门究竟都经历了什么?刺激政策失去效果,政府加杠杆并未能带动私人部门加杠杆,反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开始去杠杆,至今都未恢复至历史高点。
充分了解当时日本各部门的行为,才能客观看待为何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带动私人部门需求复苏,什么缘由导致日本私人部门最终都步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1980-1989年,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等渠道累计融资539万亿日元,主要购买土地和金融资产,较少投向厂房等固定资产。1989年不含土地的非金融资产增量甚至为0.
作为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居民部门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巨额收益后,日本居民部门购买不动产和金融资产。
1989年,居民购买了58万亿日元的不动产(住宅),较1980年增加73.4%;15万亿日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增长77.1%;25万亿日元的保险和养老金准备金,增长279%。
1989年,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贷款同比分别为14.1%和18.9%,均高于总贷款增速(9.9%),制造业贷款增速甚至是负值,为-0.4%。
二、泡沫破裂后,企业破产,开始去杠杆;居民提前还贷;金融机构发生破产潮。
1991年,企业破产数量突破1万家,债务总额超8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倍。为了存活,企业卖出土地和金融资产,回笼现金流,并继续削减负债,企业杠杆率从1997年的136.9%骤降至2004年的99.2%,减少37.7个百分点。
居民财产性收入锐减,薪酬增速放缓,既然财富无法增值,选择提前还贷减少负债。
1991年后,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速告别两位数,次年转负,且收入降幅高于支出。员工薪酬增速变缓,于1999年转负。仅靠财富收益就偿还借贷的局面消失。因此贷款利率下调至低位,却没能刺激居民加杠杆买房,反而导致了提前还贷潮。
金融机构资产端遭受三重打击:一是住专破产,给母体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带来5.73万亿日元的巨额亏损;二是企业破产数量迅速增加,无法偿还的债务沦为坏账,中小银行率先遭受危机;三是银行持有股票价值腰斩,1989年金融机构持有股票价值311万亿日元,3年后腰斩,导致银行资产迅速缩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对日本经济 “雪上加霜”,金融机构破产潮来临。
为处理破产金融机构,1992-2002年间,政府提供金融援助1.89万亿日元,资产购买支出0.37万亿日元,并投入60万亿日元增加整理回收机构的银行资本。1991年起,政府财产性收入增长转负,税收收入增长放缓,但社会转移支出增长加快,政府曾高达30万亿日元的净储蓄在1998年沦为负值,被迫大举借债。
三、日本经验显示,前期杠杆囤地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及支持其行为的金融机构受伤最深。
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供需格局注定了这一期间的房地产具备较强金融属性,而地产溢价最终来自土地。这意味着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兼具“金融属性”,价格随之走高。为攫取超额收益,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在所难免。但日本企业循环买地质押,金融机构迂回业务限制的高风险操作,为后续破产清算埋下了伏笔。
城镇化红利结束之后,前期大举购买土地并进行杠杆操作的主体,将会面临去杠杆压力,这是曾经日本实体和金融企业走过的路径。
在“失去的”三十年间,居民和私营企业在内的私人部门停止扩表,开始去杠杆。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扩张,最终超过了250%。
泡沫前后,日本各部门究竟都经历了什么?刺激政策失去效果,政府加杠杆并未能带动私人部门加杠杆,反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开始去杠杆,至今都未恢复至历史高点。
充分了解当时日本各部门的行为,才能客观看待为何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带动私人部门需求复苏,私人部门最终都步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1980-1989年,非金融企业部门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和附有新股认购权的债券等渠道疯狂举债。
这一期间企业的负债增幅达到205%,资产增幅则略低,为145%。1989财年末,企业部门债务总额达1597万亿日元,资产总额为1938万亿日元。企业债务增幅高于资产增幅,资产负债率迅速从66.2%增加至82.4%。
企业部门累计融资539万亿日元,其中银行贷款297万亿日元、非股票证券76万亿日元,股票及其他股权62万亿日元、其他负债104万亿日元。银行贷款占融资规模的比例从1980年的72.4%,下降至1989年的42.4%,其他非贷款渠道融资占比明显增加。
企业借来海量资金,主要购买土地和金融资产,而较少比例投向了库存、厂房等非金融资产。
1980和1982年,企业部门还是土地的出让方,而从1983-1993年,企业部门累计购买72万亿日元。
对比土地的净购买规模,企业部门每年购买的金融资产则更多。1980年,企业部门购买的金融资产(不含现金和存款)规模为5万亿日元,而到了1989年,已超过57万亿日元,翻了10倍。
1980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增量中,不含土地的非金融资产增量占比为60.5%,而到了1989年,这一比例甚至跌破0,也就是说当年企业部门多达95万亿日元的资产增量全是购买土地和金融资产所致。
对比制造业和大企业,中小、非制造业企业则依靠长期借款,购入了更多土地。
考虑企业大举购地和地价上涨因素,1984年至1990年,企业的持有土地增值了280万亿日元。按规模划分,中小企业持有土地增值占比更大,达68%;按产业划分来看,非制造业企业持有土地增值占比为83%,远高于制造业企业,并且多数为中小非制造业企业。
日本非金融企业把从银行和股权筹来的海量资金,拿来买地炒股,抵押套现后继续炒地,循环买地质押造就了其资产规模飞速扩张的“假性繁荣”,背后其实是靠负债快速扩张换来的。
银行对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贷款的积极性远高于制造业。1989年末,日本银行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业占比达到12.2%,而在1980年仅为5.8%;金融服务与保险业占比达到11.2%,制造业占比则降至16.0%。
银行放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变相鼓励企业购买土地等不动产,刺激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土地增值便于企业获取更多贷款,如此循环买地质押,造就了异常火爆的土地市场。
商业用地价格涨幅远超住宅和工业,1981-1991年,商业用地价格上涨113%,而工业和住宅用地价格只上涨了75%和85%。
1989年起,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再贴现率从1989年5月的3.25%,迅速增加至1990年8月的6.0%,导致融资成本飙升。
同时,大藏省要求银行对房地产业融资进行总量控制,明确规定房地产业的融资增速要低于总贷款增速。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在1989年高达14%,而到了1990年仅为3%。
日经指数在1990年下跌38.4%;东京住宅用地价格指数在1990-1991年的跌幅达33.8%。
随着资产价格暴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明显恶化,企业持有的土地和金融资产迅速缩水。
1989年末,非金融企业部门持有价值573万亿日元的土地、912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分别占总资产比重的29.6%和47%。到1992年,土地和金融资产分别较峰值减少了15.5%、19.4%。
资产贬值的同时,企业部门融资规模也断崖式下降。尽管1991年后利率大幅下降,但企业部门从外部募集资金规模持续减少,1997年后净融入资金甚至转为负值。
1989年,企业部门的融资规模高达119万亿日元,第二年降幅就达到了38.5%,并且降幅还在扩大。
日本央行从1991年7月至1995年9月,先后9次下调贴现率,贴现率从6%下降至0.5%的低水平。
然而,日本企业部门从银行的净融入资金在1994年转为负值,也就是说企业银行贷款不但没有增加,还在减少,与5年前高达50万亿日元的规模形成强烈反差。
东京工商研究所统计了债务总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1990年,这类企业破产数量为6468家,债务总额不足2万亿日元,而仅仅时隔一年,企业破产数量突破1万家,达到10723家,破产企业的债务总额超8万亿日元,翻了三倍。
此后破产企业数量还在增加,到2000年,破产企业数量达到18769家,债务总额近24万亿日元。
企业部门选择忍痛割肉,卖出土地和金融资产,旨在回笼现金流,避免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而破产。
日本地价在1991年达到巅峰后,一直下行至今,企业不停出让手中土地,仅1994年,净卖地规模就达8万亿日元。1991-1993年,企业部门净卖出了约37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其中11万亿日元的非股票证券、4.7万亿日元的股票及其他股权、15.5万亿的其他非金融资产,现金和存款也减少了5.6万亿日元。
以日本大型房地产企业三菱地所和三井不动产为例。三菱地所在1989年10月花费14亿美元收购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而在1996年,却将洛克菲勒中心以3.08亿美元的价格(含8亿美元债务)卖出。这笔交易中,三菱地所损失超10亿美元。
三井不动产在2000年出售Oriental Land(东京迪士尼运营方)的股权,虽回笼304亿日元资金,但每股售价仅有IPO的六成。
存活下来的企业持续削减负债,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1997年的136.9%骤降至2004年的99.2%,减少了37.7个百分点。
1997-2004年,企业融资规模累计减少171万亿日元,其中,银行贷款减少120.5万亿日元,非股票证券减少33万亿日元,其他负债减少63.7万亿日元。唯有股票及其他股权融资有所增加,这一期间累计融资为46.3万亿日元。
日本是以私有为主、国家和公共所有并存的多元土地所有制。2013年,全国的私人土地占比为43.4%,远高于国有、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公有地,其中三大都市圈私有土地占比更高。
作为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地价飙涨使居民部门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1980-1989年,居民部门资产增长了160.2%,规模达到2622万亿日元。其中土地资产从476万亿日元增长至1371万亿日元,涨幅为187.9%。
居民的负债以银行贷款为主,这一期间贷款上涨145%,规模为254万亿日元。地价飙涨使居民部门资产增幅高于负债,资产负债率下降1.3个百分点。
泡沫期间,居民部门是土地的主要出售方,仅1990年,就卖出26万亿日元的土地。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巨额收益后,日本居民部门购买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并进行储蓄。
1989年,居民购买了58万亿日元的不动产(住宅),较1980年增加73.4%;15万亿日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增长77.1%;25万亿日元的保险和养老金准备金,增长279%。
泡沫期间,居民部门仅靠财富收益就能偿还借贷,还绰绰有余,财富规模和收益稳定增长的局面让居民敢于借贷买房和消费。
1990年,居民部门共获得59万亿日元的财产性收入,较1980年有近2倍的增幅,是当年财产性支出的2.5倍。而同期居民部门偿还的房贷仅为9万亿日元,消费贷为7万亿日元。
财产性收入占薪酬的比重不断增长,从1980年的15.9%,增长至1990年的25.6%。
然而,泡沫破灭后,财产性收入骤降,薪酬也停止增长,居民部门财富增值的美梦破碎。
1991年,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速告别两位数,次年转负,并且收入降幅高于支出降幅。财产性收入与支出之比从1992年的2.5,迅速下降,2003年仅为1.44。
同时,员工薪酬的增速放缓,于1998年转负。财产性收入与员工薪酬之比在2003年仅有8.1%,不足1990年的三分之一。
1995年,日本再贴现率降至0.5%低位,房贷利率早已从5.5%的高位降至3%附近,然而,提前还款额却创历史新高,达到了9.9万亿日元。
居民部门每年应付的房贷利息从1991年逾9万亿日元,减少了三分之一,2000年后再也没超过6万亿日元。
同一时期,日本居民应付的消费贷利息规模也在缩小。1992-2007年,消费者债务利息年均同比增速为-0.9%,而在1991年及以前,是高达2位数的增速。
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下辖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不同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和面临的监管力度有着很大区别。
国有金融机构包括邮政储蓄和二行九库,与国内政策性银行类似,其首要目标为响应国家政策而非盈利。
民间金融机构分为存款式和非存款式。民间存款式机构包括商业银行、长期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农林渔业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根据规模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又被分为都市银行、地方银行和第二地方银行等,都市银行是日本银行业的核心,在日本的地位可以类比国有六大行,地方银行则类似于国内城商行农商行。长期金融机构包括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主要从事长期贷款业务,前者资金来源主要为发行债券,后者为信托。
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中小企业信贷,分为信用金库和信用组合。信用金库是日本的合作性银行,其客户主要以日本城市地区的中小企业为主,实行会员“无论股份多少,均一人一票”的经典合作制模式。信用组合是根据 《中小企业互助合作法》 建立的中小企业的职工组织和带有互相扶助性质的金融机构。信用组合有更为明显的互助合作性质。
信用组合所受监管更为宽松,信用组合不良贷款率始终遥遥领先,在2007年以前远超10%的国际警戒线,是最先破产的一类金融机构。信用金库的不良贷款率居次,波动较小。都市银行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居于末位。
此外,为规避监管和扩张业务规模,银行设立其财务子公司——住专向房地产业的“迂回融资”。
“住专”是日本住宅专业金融公司的简称。1970年前,日本政府禁止金融机构向个人提供住宅贷款。1971年,在大藏省支持下,以银行为母体、对私人提供住房信贷的第一家住宅专业金融机构成立。到1976年,一共有七家住宅公司。
住专本身不是银行,不能吸收存款,只能依托于某一母体商业银行的支持而存在。许多母体银行不方便直接放贷、或者风险较高的项目,都由自己属下的住专接手。
1980年后,住专突破《贷金业规制法》的限制,业务从个人住宅贷款扩展到向企业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住房贷款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95.6%,降至1990年的21.4%,向企业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则由不足4.4%上升到78.6%,规模由 1400 亿日元上升到 9.6 万亿日元,在整个房地产融资市场中的份额也增至11.8%。
住专的资金来源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的拆借资金,如农林渔业金融机构;七家住专公司的股东除银行外,也包含证券、保险等。给今后住专破产危机会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
农林渔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系统内的存款和发行债券,贷款对象主要针对农业团体。农业系统收取的存款明显大于贷出,可以利用充裕资金给其他机构拆借或投资。
泡沫期间,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贷款增速高于总贷款增速,银行新增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
1989年,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速为14.1%,金融保险业贷款同比增速为18.9%,均高于总贷款增速(9.9%),而制造业贷款增速甚至是负值,为-0.4%。
战后日本实行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又是企业最大的股东。
所谓主银行制度,是指企业将一家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银行,并允许其持股,具有投票权。在这一制度下,银行与关联企业几乎是一体,一荣俱荣。
通过实施主银行制度,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日本建立起以银行为中心的巨大企业集团。如三井集团、三菱集团、住友集团、富士集团,就分别是围绕原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和富士银行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当企业陷入困境时,即使抵押资产在不断缩水,作为股东的银行还是会选择施以援助,继续发放贷款。
1990-1997年,资产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持有的土地和金融资产迅速缩水,金融机构却依旧发放了累计规模达417万亿日元的贷款。
房地产公司还款困难,导致当初通过信用下沉扩大贷款规模的住专公司,如今坏账问题浮出水面。
1995年,根据大藏省测算,7家住宅金融专业公司贷款总额共计13万亿日元,坏账规模达6.4万亿。当年有四家住专公司公开宣布失去还贷能力。
在大藏省的协调下,债权人减免了6.41 万亿日元的债权。住专共计规模为 6.41 万亿日元的债权。其中,母体银行放弃在住专的全部债权,也就是 3.5 万亿日元,其他债权人放弃 1.7万亿日元的债务。剩下的 1.21 万亿日元的债务中,由农协类金融机构承担 5300 亿日元,再用财政资金承担 6800 亿日元的债务损失。
在本轮住专危机中,金融机构累计承担了5.73万亿日元的损失,这导致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明显增加。1995年不良贷款规模相较于1992年增加了71%, 不良贷款率陡增至6.1%左右。
其次,企业破产数量迅速增加,无法偿还的债务沦为坏账,服务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率先破产。
前文已经提到,仅在1991年,破产企业数量就突破1万家,债务总额超8万亿日元。最先破产的多是中小企业,这造成主要服务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遭受危机。
1994年,协和信用组合和安全信用组合破产,揭开了金融机构破产潮的序幕。
三是,前期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持有的企业股票价值,在资产价格暴跌后遭遇腰斩,造成银行资产缩水。
1989年,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多达311万亿日元的股票及其他股权,而到1992年,仅有143万亿日元,减少了54%。
起初,日本通过“护送船队”机制让大型金融机构兼并陷入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但是这一举措反而让大型金融机构承担了巨额亏损,也遭遇危机。
“护送船队”制度,是形容战后日本金融体系犹如一支船队,政府的行政指导和各种金融监管措施都是为了保护这支船队的每一位成员不掉队,顺利到达“胜利的彼岸”。也就是说大型金融机构会对破产金融机构实施援助。
早在1991年地价大幅下跌时,中小房企出现经营困难,住专公司坏账问题开始暴露。于是在1992年,大藏省引入农协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作为住专的周转资金。到1995年住专公司破产时,农协类金融机构已成为住专最大债权人,以“赠与”名义承担了5300 亿日元的损失。
随后,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不良债权处置机构。1996年不良贷款率和规模均较1995年双双下降。不良贷款率由6.1%降至4.7%,规模由28.5万亿日元,降至21.8万亿日元。
1994年,由日本银行与非国有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东京共同银行,为破产的协和信用组合与安全信用组合提供援助。1995年,日本政府采取同样的方式,对破产的Cosmos信用社、木津信用社和兵库银行进行处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财务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出资弥补贷款损失和赔付成本之间的缺口。1996年,由存款保险机构出资,东京共同银行改组成为整理回收银行,后来与住专债权管理公司合并,成立整理回收机构,接管已破产的金融机构,回收处置不良债权。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对日本经济 “雪上加霜”,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不良贷款率和规模再度回升。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是日本向亚洲的出口减少,1998年1月至9月,日本对亚洲出口同比减少25%;二是日本在东盟四国及亚洲四小龙等地区所持有的投融资债权遭受巨大亏损,仅日本银行贷款余额一项就超过2500亿美元,各国货币暴跌产生的汇兑亏损,更是导致债权价值很不稳定。
日元迅速贬值。1995年末,美元兑日元汇率为103.5;而1997年末,达到了130.6。
金融机构破产潮来临,北海道拓殖银行、三洋证券、日产生命接连破产,成为破产潮中第一家破产的大型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
北海道拓殖银行是北海道地区最大、全日本第十大的商业银行,破产时的坏账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日元。
1990年到1997年的8年熊市,成为日本证券破产的导火索。股票买卖手续费收入减少、自营业务亏损、用自有资金对大客户损失进行补偿等系列因素,造成证券陷入危机。紧跟三洋证券破产,日本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倒闭。
当时日本寿险公司经营的产品以固定利率的传统年金险为主,在银行降低利率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面临巨额利差亏损,保险公司破产也难以避免。
不良贷款规模达42万亿日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不良贷款率达到8.4%。
资产价格飙涨,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随之升值,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明显快于负债,资产负债率被动下降,从1985年的63%,降至1990年的47%。
1990年末,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规模超642万亿日元,较1985年增长了70%。而负债规模为301万亿日元,仅增长26%。
这一期间,政府收入也迎来快速增长。税收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幅分别为46%和54%,而同期社会转移支付和财产性支出的增幅分别为36%和15%。
如前文提及的利用财政资金承担了住专公司6800 亿日元的债务损失。1992-2002年间,日本政府为破产金融机构提供了金融援助1.89万亿日元,约占74.7%;资产购买支出0.37万亿日元,约占25.2%。
随着不良债权危机引发金融机构破产潮,日本政府投入60万亿日元在整理回收机构开设三个账户,将公共资金以正常的会计手续转入银行账户,增加银行资本。
1999年,整理回收银行与住宅金融债权管理公司合并成整理回收机构,负责接收破产金融机构,处置其不良资产。政府在投入的公共资金多达60万亿日元(使用限度),为保证银行支付能力建立了“特别保险账户”,为帮助银行清理不良债权建立了“金融机能早期健全化账目”,为接管破产银行建立了“金融重建账目”。
不良贷款处置损失规模与政府处置力度紧密相关。1996-1999年间,不良贷款处置损失处于高位,此后逐渐下降。1996-1999年间不良贷款处置损失高达48万亿日元。
自1991年起,政府财产性收入增长转负,从峰值12万亿日元,降至2003年的7万亿日元,减少了39%。
税收收入增长放缓,1981-1990年期间年均同比增速为7.0%,而1991-1998年期间年均同比增速仅为2.8%,并于1999年开始负增长。税收收入在1998年约为44万亿日元,2009年已经跌至38万亿日元。
在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转移支付占据主要比例,1980年,转移支付为38万亿日元,到2009年,规模达到131万亿日元,增长了243%。
政府部门净储蓄在1991年一度规模超30万亿日元,而到1998年沦为负值,此后再也未能转正。
政府融资中以债券等非股票证券融资为主,1991年,非股票证券融资规模为5万亿日元,而到1999年,这一规模高达54万亿日元,翻了近10倍,此后长达6年,非股票证券融资一直保持年均约50万亿日元的规模。
消费复苏的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开始回暖,但恢复水平有限,未来延续低位震荡,还是能继续向常态化增速靠拢,仍需密切跟踪。消费如持续乏力,则经济回升动力受限。
地产行业能否继续改善存在不确定性。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当前出现短暂回暖趋势,但多类指标仍是负增长,未来能否保持回暖态势,仍需观察。
海外政策力度或超预期。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讲究数据依赖,如果经济数据发展远离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力度或超预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转向速度或过快,引发通胀快速下行。需要警惕海外经济政策转向的风险,密切关注各国央行政策立场变化。
地缘政治发展或超预期。日本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存在脆弱性,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发展对日本造成高度不确定性。
周君芝: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曾获2023年wind第11届金师宏观第一;2023年21世纪金师宏观第四;2023年第11届choice最佳分析师宏观第三。曾于2017-2020年连续四年荣获“新财富”宏观第一名(团队核心成员),2017-2020年连续四年荣获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第一名(团队核心成员)。